《弟弟的演奏》:“屎尿屁”背后一代人的青春
读书笔记
朱文乃狂狷之徒,他把现代社会中虚伪的道德撕扯殆尽,通过这个薄薄的小册子,用一种尖锐无比的声音呐喊并对之发出令人发指的控诉。遍布全书的屎尿屁和猥亵性语言并没有赋予这部作品淫秽的特质(但你不得不承认其语言因此显得极为散乱和令人难以忍受),相反,它呈现出一种令人难过无比的无奈和压抑来。
朱文的笔调无疑是戏谑的,这是一种贴近后现代主义气质的黑色幽默和荒诞书写,从中我们能够看出一副与主流叙事截然不同的80年代大学生群像。陈晓明教授将之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加以对比,他指出:相比充满挑衅意味横冲直撞于文坛的朱文而言,刘索拉、徐星之作“不过是一些温文尔雅的古典浪漫主义而已”。
在这部作品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都是毫无下限的,福斯特所谓的“平面人物”。他们丝毫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品质,反而通过其言行举止一而再再而三地印证了叙事者声称的“杂种”称谓。在叙事行进的过程中,我们对他们的观感(我说的是最表面的那种)将不断且恒久地停留在鄙夷和唾弃之中,世人无法想象本应在那个时代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的大学生们竟然具有这样一种嘴脸。朱文的戏谑是一种刻意地夸大,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甚至可以料想到他在书写时嬉皮笑脸、呲牙咧嘴的狰狞面目(如果真如李冯所说这个朱文是一个十分正常甚至极度健康强壮的理工男子的话,其人其文确实带给了我一些割裂感),通过这种方式,他将正常的人物重塑为漫画式的形象,继而通过这种重塑完成了他对时代和人群的解构。我们实在难以将朱文笔下的“南方以北”们跟张贤亮在《北方的河》中笔下的那位充满理想情怀的备考大学生以及刘震云《塔铺》中的那些学子联系到一起。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状态:理想的失落似乎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事实,经过89大事件和90年代的市场化大潮,最淳朴的风气已经离人们而去,留给他们的只剩下如洪水般席卷而来的消费、拜金和享乐主义思潮。
尽管陈晓明教授更多将“性饥饿”作为这部作品的核心,将“性”作为朱文所谓“本质性写作”追求的“本质”,但笔者却认为“性”在这部作品中带有一种若有若无的隐喻意味,更确切地说,“性”——这篇小说毋庸置疑的主题实际只是一个表层,蕴于其中的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衰落气质,这与我刚刚提到的政治理想失落和市场消费社会的刺激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朱文通过其书写塑造出的并非仅仅是学校的生活状况,通过夸张、荒诞和变形的非常规书写手段,发生在校园中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写照,作为“未来栋梁”的大学生们进入社会之后将自然而然地成为“支柱”,因而“杂种”当道的社会就是“杂种”当道的大学的未来。
值得关注的是朱文在小说中运用的语调,那是一种破罐破摔、狼心狗肺的语调,仿佛“我们”本就不存在什么值得托付的未来,这是一种命定里的颓丧:“我们的身体有着堕落的惯性,你越是想遏止,它就会表现得更加不可遏止”,所以他们就甘愿在烂泥塘里,时不时扑腾一下,不过是为了找到烂泥塘中更能另自己安逸的位置罢了。理想的失落感是如此强烈,他们就这样望着时代奔涌前去,他们没有办法,也压根就不思考办法,他们就这样无怨无悔地沉浸在无知迷茫之中,除了朱文,李冯的《在天上》和贺奕的《伪生活》也同样属于这个谱系,在这些作品里,大学生们“悬浮在空中”,他们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裹挟在性欲和财欲之中无法自拔,他们的精神正是一种失落的精神,他们所过的也是一种“在天上的伪生活”。
至少,我是说至少,这些并不为人所关注和喜爱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中的这批人(“晚生代”也好“六十年代作家”也好,管他叫什么呢)的一个“精神坐标”,他们面对飞快流转的中国社会感到深深的无所适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称之为一个“过渡的时代”。当原本由政治带来的理想辉光再度暗淡无光,甚至遭到经济巨人的疯狂碾压,这群本就被难以划分的作家或许会更多地感到某种不适,所以他说“我尊敬这些就要不能勃起的先生们”(虽然这句话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所以他在谈到“比我父亲还老的人”的时候感到某种愉快,“因为眼下也就只有他们谈起性来还有那么一点可爱的天真。”这实际上表达了这位狂士的一种羡慕情绪,“他们是没有性病的一代人,他们成功地把性幻想变成了远大的理想,成功地把致命的女人变成了可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民,成功地把狭隘的床第变成了广阔的祖国大地。你知道,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闪耀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性啊。”我们不妨把这段话视为朱文的某种自白,尽管这批人发动了那场名为“断裂”的“闹剧”,表达了自己对老前辈们的不屑一顾和完全的否定,但我们不能就因此认定其思想就是如其在宣言中表述的那样,毕竟在现代传媒观念完全介入的情况下谁又能完全肯定这场“闹剧”并非一次演技逼真的“作秀”?人、文结合似乎才更符合我们作出判断时应该具备的观念。
绕了这么一大圈,我的意思其实是想说,即便是对十七年乃至文革时期极度厌弃的狂士,他也无法否认自己对当时纯粹无比的理想主义的向往,同时这也并不同他以及同一批作家在另一个方面深耕以找寻自己这代“夹层者”立足的基点相对立。从这个角度看,这本由“疯言疯语”构成的“污秽”之书实际上有着一种批判和锐意进取的精神,也正是这样一种亲历污浊之后的“清醒”树立起了他们在文坛的立足之地。
文摘
那是一个勃起的年代,人人都开始正视自己的勃起,人人都学着不用头脑而用龟头来思考。社会也在勃起,经济也在勃起,科学也在勃起,文化也在勃起,体育也在勃起,连同政治体制也在勃起,但是就是有点举而不坚。儿童提前勃起,少年人正在勃起,青年人当然勃起,中年人吞下了春药,继续勃起,老年人因为无法勃起而痛心疾首,所以他们看不惯这也看不惯那,整天骂骂咧咧,怀念他们美好的从前,也就是怀念他们能够勉强勃起的那些岁月。太可怕了,整个世界都在抱怨内裤太紧,于是你走到哪都能听到沮丧的拉得长长的早泄的尾音。发财的梦早泄了,成功的梦早泄了,美国的梦巴黎的梦日本的梦还有土耳其的梦统统早泄了……换上一条干净的内裤,就到了九十年代。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早泄以后顽强地坚持着企图再次勃起的伟大时代。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西服。当时是深秋,空气像稀释以后的精液,灰白色的。我很后悔没有径直赶到照相馆去,拍上一张标准照。然后洗上一百张,用在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结婚证、护照、寻人启事、讣告等等所有在我的一生中可能用得着的地方。当我的身体不再发痒的时候,我感觉好极了,我觉得我终于成了一个他妈的体面人,我希望我尊敬的父母在这个时候见到他们的孩子,我希望我的老师在这个时候重新对我恢复信心。
现在我总不失时机地和比我父亲还老的人谈论他妈的性。那样的谈论,对我很有帮助,因为眼下也就只有他们谈起性来还有那么一点可爱的天真。他们是没有性病的一代人,他们成功地把性幻想变成了远大的理想,成功地把致命的女人变成了可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民,成功地把狭隘的床第变成了广阔的祖国大地。你知道,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闪耀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性啊。
我的下面仍然很坚挺,只是顶得有点痛。有的朋友顶得比我还痛,从北方跑到南方,从宽敞的街道到狭窄的阴道,从落后的中国跑到先进的美国,那玩意还硬邦邦地顶着;从默默无闻到大名鼎鼎,从饥肠辘辘到腰缠万贯,从少年老成到鹤发童颜,那玩意还硬邦邦地顶着,让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是一台性能良好的液压机,那条细细的管道里越来越高的压力经过另一些管道传递上去,一直传递到你的脑袋里,就成了难以克服的野心欲望。你了解你自己吗?你这个白痴。
我决定在楼下的台阶上歇上那么一会儿,那件西服当然得垫在我屁股下面。虽然我的裤子比台阶更脏,但是我还是把那件西服垫在下面,它应该在我下面,那个他妈的优等生应该撅着屁股在我下面。我把一个体面的身份垫在下面,于是就有一阵凉爽的风拂面而来。那是一阵八十年代初的秋风,刚刚有些淫秽放荡的苗头,更多的是无所适从。
生活近在眼前,他们却还要去啃那些没用的书本,真是不幸。
这个世界步入青春期以后,很多很多的家伙都不太会走路了。
有一次和建新喝酒,各灌了十瓶啤酒下去以后,建新忽然严肃地对他说,我觉得自己已经快死了,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天啦,我们一下子兴奋起来,太好了,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看来是患了绝症,就要死去。终于有些事情了,这真是太好了,虽然没说出口,但是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于是我们开始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希望有一天清晨醒来,发现建新已经在床上死得硬硬的,到时我们将争先恐后地扑上去抬胳膊抬腿,把他抬到那座建于一八九三年的礼堂去,把他抬到大街上去,把他抬到这个城市最高的那座三十七层的大饭店的顶层璇宫去,然后从那里把他扔下去,让他的长发迎风飞起,让他有机会像一只小鸟那样飞翔那么一次,然后我们这些剩下的幸运的家伙就把身上的硬币凑起来,找个小酒馆去喝上那么一顿庆祝一下,另外在摸摸阄,看看下面该谁为我们大家生他妈一场绝症。
我们的辅导员最后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不出话来,他对我们失望极了,站在他周围的是想吃屎的一代年轻人。
区区几个屎橛就让我们这群自命非凡的伪善的家伙统统现了原形,它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边界。我们难以克服表哥的屎橛,我们多么让自己失望啊。面对脸色已经有了一点红润的表哥,我在心里咒骂那个想出风头的南方以北,他无意中给了我们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嘴脸,和我们恶毒攻击的那些白痴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小丑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
那会儿的条件真是艰苦,为了一次性生活,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城市,希望能找到一个安全一些的地方。有时我们已经精疲力竭,却仍然一无所获。走在夜晚的大街,看着万家灯火一盏一盏地熄灭,我们就难以控制我们芒刺般的嫉妒。全世界都在快活,除了彳亍而行的我们,你说这算是个什么世道。这个城市大概有五百万人口,据我们保守估计,一个晚上至少有一百万次射精,也就是平均每秒钟就有三十多次成功的射精,还不包括流动人口的,不包括猫狗以及老鼠的,为什么其中就不能有我们一次呢?
该死的性幻想刺激着一个男人卑劣的德性,它使你空前地狂热,它使你忘乎所以,而一切又必须在黑暗中进行,在无声中进行。
但是亲爱的,我还能说什么呢?认识你以前我就已经是一个烂了一半的人了,我还要烂下去,因为我已经烂出了一点价值感,烂出了一点意思,我的生活就是继续烂下去。
走,我们顺着肉体的惯性继续堕落下去吧。不管在怎样的一个名义下,我们的堕落勇往直前,势不可挡。
我这个人净扯一些没有必要扯的谎,没有明确的目的,也不能带来乐趣,扯的谎也没有想象力,听的人心里难过,说的人心里也不舒服,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扯下去。也许这是我的一个习惯,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也不指望它给自己带来好处,这个习惯的本质就是无聊,就是没边没际的无聊,就是如影随形的无聊,就是要了我的命的无聊。
学校里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教室都亮着灯,更显得空空荡荡。我们就像在一则故事的结尾来到了这里一样,每一个动作都会让自己觉得是多余的,是他妈的没有必要的。
胃还是原来的胃,但是杂种们的胃口已不是原来的胃口。我们要吃,你们要吃,他们也要吃,大家都要吃。吃下去的丰富多彩,拉出来的依然单调无比。想到这一点,大家才稍微心定了一点,妈的,生活还是可以把握的。
我们现在最听不得这种话了!谁胆敢再拿希望、未来、明天来刺激我们,我们就叫他滚蛋!我们决不再受骗啦!
没过多长时间,我的同事、我的领导就不再把我当作一个体面的人来对待了。其中的原因没人愿意跟我讲清楚。妈的,什么叫体面?他们不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告诉我像我这样的就叫做不体面。我的长相无可挑剔,我的穿着我可挑剔,我的家庭无可挑剔,我的文凭无可挑剔,难道说,是我的灵魂不体面或者不够体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也没办法好想了,就请你容忍我吧。再来一遍:就请你容忍我吧。
这年头富人有富人的玩法,穷人也自有穷人的玩法。穷人玩不出富人的趣味,富人也尝不到穷人的乐子。但是我这个人既不是富人也不是穷人,不阴不阳,所以我只能继续采纳我故有的玩法。现在我要习惯一个人烂下去,那就是单纯的烂,烂一点是烂,烂到底也是烂,你绝对别想烂出一点价值感来,你绝对别想边烂边以叛逆者自居。
我们的身体有着堕落的惯性,你越是想遏止,它就会表现得更加不可遏止,这大概就是秘诀。
我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准备着和这个世界通奸的人。
栾玲来到我的生活中,就像是给我毕业后那段时光的一次总结。只要看看每个时期你和什么样的女人在一起,就知道那个时期你混得怎么样了。现在我的状况确实像那个饱经沧桑的栾玲那样糟糕,那么我又有什么必要回避这一点呢?这是你的现实。再来一遍:这是你的现实。在激情丧失的尽头,我没想到厌恶也能成为另一种激情。
我还得感谢你,栾科长,你使我头脑从没有过地清醒,我知道我的热情没有方向,没有结果,没有意义。我只是我自己无情的挥霍者,我只是自己野蛮的入侵者,我只是自己怀抱着一肚子虚情假意的恋人,我只是自己没有一丝忠诚可言的背叛者,我只是从自己这块土地上茫然走过的行色疲惫的路人。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我坐在办公室的地板上,抽着烟,顺着百叶窗倾斜的整齐的缝隙看上去,我看到了正在不紧不慢地流动着的时间。
我有好久没这么兴奋过了。我同宿舍的同事平常和我不太啰嗦,但是这一次也忍不住好奇地问我,今天是怎么啦?像中了头奖似的。我说,没什么,今天我阳萎了。什么?今天我阳萎啦!我的同事有些紧张地看看我,然后就走开去了。我从箱子里翻出我的毕业留言册来,上面有建新南方以北那些杂种的信址。我一口气写了七、八封信,每封信上都只有一句话: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我阳萎了!连夜我就去邮局把信塞到了那只邮筒里。但是我仍然感到意犹未尽,于是我晚饭没吃就上了大街。下班的高峰期已过,但是大街上的车辆和行人还是非常多,大家喜气洋洋的,就像过节一样。是啊,我终于萎掉了,过节了。一辆单车从右侧的一条巷子里斜穿出来,从后面一下子把我撞了一个跟头。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从地上爬起来,一个劲地向我陪不是,他说车没刹,实在控制不住。我起来拍拍他的肩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今天我萎掉了,所以没关系的。那个年轻人千恩万谢地走了以后,我才觉得我的右腿疼得厉害。我就这么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不远处有部公用电话,我把口袋里的零钱都翻了出来。一位姑娘正在给她的男朋友打电话,嗓音甜得让人发腻,而且说起来就没完没了。我对她说,快点,我有急事。这个姑娘非常不乐意地一扭身子,背对着我继续和她的心上人倾诉起来。我实在等不及了,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喂,我说,今天我阳萎了。什么?今天我萎掉了。那位姑娘电话一扔就跑了,连钱都没付。我拿起电话,把我记得的号码都拨了一遍,因为我没有多少零钱,所以每个电话我都尽可能地说得简略一点,喂,你好,今天我萎掉了,没其他事,就这样。打完电话以后,我一瘸一拐地走到了鼓楼广场,我站到了广场的中心,我展开双臂,朝着天空,大喊:今天我阳萎了!今天我萎掉了!哈哈!所有的车辆绕着转盘急速地旋转起来,所有的行人围着转盘急速地旋转起来,所有的声响绕着转盘急速地旋转起来。后来我累了,而且肚子也很饿,我就爬上了天桥去休息一下。天桥上已经有了一个人,一脸的胡子,正趴在栏杆上往下看,他看起来很忧郁,好像对我的出现感到很不满。你看你的风景,我喘我的气,妈的,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不时地转脸警惕地盯我一眼。我没精力理他,我要喘气。过了一会儿,这个杂种大概觉得我没什么恶意,就放松下来。喂!我朝他招招手。叫你呢!对,叫你呢!他有些迟疑地向我走了过来,干嘛?我轻声地对他说,今天我阳萎了,萎掉了。我吃惊地发现这个杂种的脸在神经质地抽搐着,天啦,我做错了什么了吗?这个杂种猛然冲了过来,抱住我的两条腿,就想把我往天桥下掀,嘴里恶狠狠地骂着,妈的,你敢骂我阳萎,看老子杀了你!我拼命挣扎,等等,等等,你听清楚了,我是说,今天我阳萎了!是我!我!大胡子杂种这才放下了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妈的,你到底是说谁?我指着自己的鼻子,我说我,我今天萎掉了。噢,是这样,那很好,很好,他对我说。他感到很不过意,举止越来越不自然,最后只好离开,把整个天桥都让给了我。但是我在天桥也没呆多长时间,我一瘸一拐地去了火车站买了当场票,一刻不停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火车颠簸完了以后,我又坐上汽车。下了汽车以后,我又上了船。上了岸以后,我就开始步行。就这样,我终于到了家。我抖擞起精神敲了敲门,我有好久没有回老家了,心情自然有些激动。开门的是我满头白发的父亲,他的手里还拿着一副老花眼镜。我对他说,爸爸,我今天阳萎了。我萎掉了。对,我是这么说的,我是想告诉父亲,我终于萎掉了,我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过我现实的生活了。
注:
摘录内容均来自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晚生代”代表作家朱文的长篇小说《弟弟的演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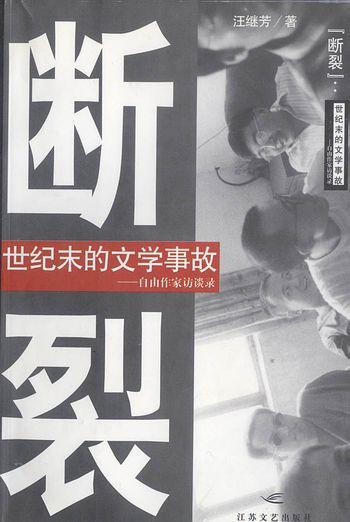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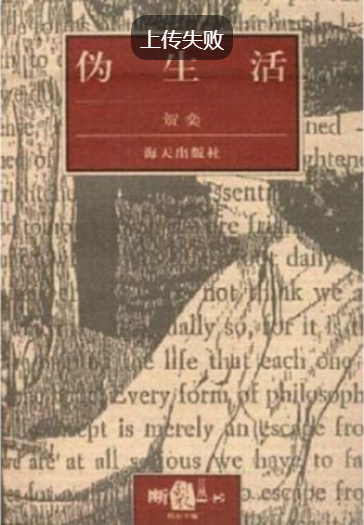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