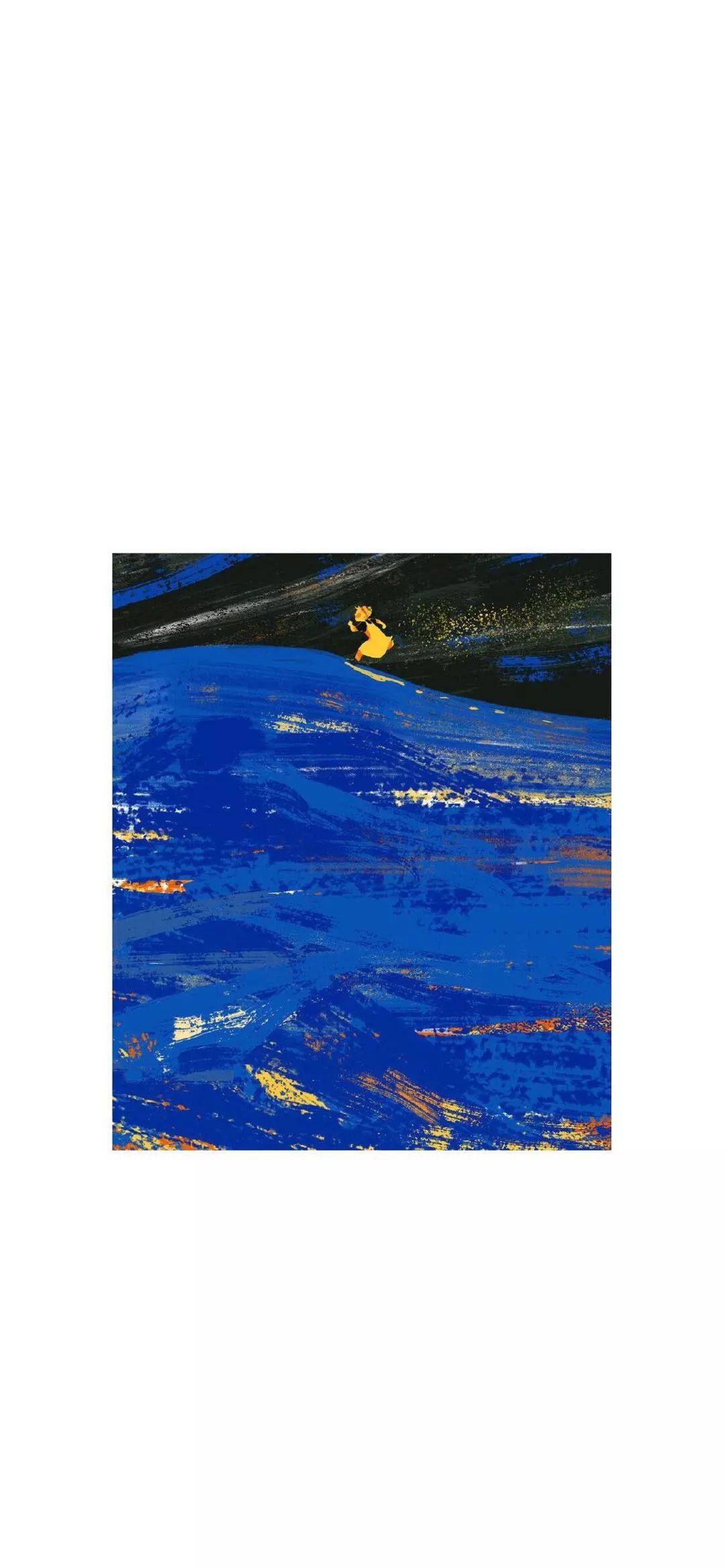《老友、爱人和大麻烦:马修·派瑞回忆录》读后: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生活有多糟糕
令人悲哀的是即便派瑞这么真诚地剖析了自己,他也还是很难获得他人的理解。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面对一个个体的时候不去说自己不要成为他这样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意识到很多事情其实并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而因为这种不能选择的东西来武断地判断一个人是多么不必要也多么可笑?
我们没有被教导成要学着理解别人,从小到大,我们只被教导成只懂得非此即彼和填写 ABCD 的白痴。然后,就按照自己很可能是粗浅鄙陋、完全不值一提的这些见解开始对自己完全无法理解也压根不愿去理解的人事贴上一个又一个不无恶意的标签,先是瘾君子,再是酗酒者,最后还得添上抑郁症。
这些标签就是被这群无知的白痴生造出来并且广为传播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仅仅为了轻易地将一个人划入一个类别之中,并由此将他与我们自己分隔开来以换取那些可悲可鄙且廉价到令人发呕的优越感?难道不是仅仅想在所谓的和平年代再度建构出毫无意义的我们和他们,建构出一种又一种新的对立?为此,我们都得装得像是真的存在这样一种不容分说的界线一样。但我们也确实都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幻想,也只是一个幻象,福柯以及他的哲学已经把这样的想法从根本上连根刨除了。好吧,即便不知道福柯,后现代主义也早已铲平了这一切,谁能说不是呢?“来嘛好兄弟,别那么严肃,我们不过是说着玩玩”,谁还不会这么一套玩世不恭,不负责任?我相信甚至根本不用学习,这已经是我们这代人以及更年轻世代刻入骨髓的基因。
我是会对马修的遭遇感到不平的,前提是我完全相信他在自传中所写的全然是真实的。但我并不真的相信这一点。我经过的训练和自己的写作经历让我本能地对人的任何自我表述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怀疑。因为我坚信,在我触摸过与他相关的其它文本之前我不可能真的了解他。这真的是一个悖论:你想了解一个人,从他自己的口中获得了想要的全部信息,却无法确信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换言之,你必须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他们对他的印象之后才能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尤其是在面对一个长期处于精神飘忽不定状态下的作者,同样在你也无法探究其写作动因的情况下。但现实确实如此,真相总是残酷且令人失望的,不是吗?不过,我想还是多少能够从笔触中看出写作者是否真诚。在这个问题上,马修是及格甚至能达到优的。尽管我还是忍不住怀疑他写作的最初动机是否真如他所言的那样是真的改过了自新,进入了人生新的阶段。对此,我只能承认自己压根不怎么了解他。
最能让我收获共鸣的部分其实是他对自己缺乏安全感的袒露以及对自我的否定。是的,请允许我开始大段摘录还有风马牛不相及的随意发疯、联想:
“绝大多数时候,我总会被困在这些缠人的思绪中:我不够好,我无关紧要,我太过渴求关注。这些思绪让我感到不适。我需要爱,但我不相信爱。如果我把我的职业,把钱德勒这个角色抛到一边,向你展示我的真实面目,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但更糟的是,你可能会注意到我,然后离开我。而我接受不了。我承受不了那种结局。再也无法承受。那会将我变成一粒尘埃,使我湮灭。所以,我会先离开你。我会在脑海中编造借口,假装你出了问题,然后我会信以为真。我会离开。”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这段文字背后与其表面截然不同的高声控诉。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了这样的人,即便我们想要改变,但实际上真正能够改变的部分能有多少?又在多大程度我们能够改变?我无法不对这些感到怀疑。倘若如此,我们是否就很难有办法找到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心理的先天性残疾难道真的跟外貌体型美丑的不公有什么区别吗?但是为什么这种存在已久的无声的“压迫”始终没有被看到?以至于我们还要进一步接受歧视。任何在对方面孔中表露出的不正常的神情都足以将我们击溃,而最终却还要怪罪到我们自己的头上。敏感,这个词我真的受够了,但我可能一辈子都摆脱不掉它,我又能怎么样呢?当我们试图摆脱它的时候却又惹上了更多的麻烦,就像派瑞所面临的那样:酒精、药品、尼古丁。我们能怎么样呢?或许,使用它们,我们能够维持表面的体面而暂时忘却自己的本来面目,不使用它们就只能在无望中等待自己暴露殆尽。无论如何,我们总会成为对自己毫不负责的大人,总是会受到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指指点点和窃窃私语。
“腹绞痛、成瘾症、贯穿一生的被抛弃感、我不够好的感觉、持续不断的不安、对于爱的急切渴求、我不重要的感觉。”
这是我们的错吗?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自己承担?凭什么就只能生来如此,低人一等(别他妈跟我说没有这回事,真的,别他妈跟我说这句话好吗)?我始终不能理解这个社会的运转逻辑:吞咽下一切不正常然后把真正正常的指责为不正常,再将它逼到死角,消灭殆尽,李代桃僵。为什么我们就对这些如此习焉不察?我想我是永远也无法理解了。
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一次又一次否认自己,然后陷入无望之中(或者短暂振作然后为了下一次更深地陷入其中)。说教多么轻松,因为接受的太多我们自己也早已习得,甚至不用他们张口,我们就已经能够口若悬河自我贬低得很全面。看,说教多么轻松,我们能一次又一次将自己贬低得一无是处,甚至能用截然不同的口吻、修辞,压根不劳他们费心。
“我不断地失去我的父亲,我不断地被丢弃在边境。尼亚加拉河的咆哮声永远在我的耳畔激荡,即便是一剂苯巴比妥也无法让其安静。外祖母会柔声哄我,给我开一罐健怡可乐,淡淡茴芹和隐隐甘草的味道让我的味蕾充满了失落。”
读来实在是令人心碎,在某种程度上,我一直在追求这样一种心碎,它对我而言就像酒精、药物、尼古丁对于派瑞一样,我是不是要庆幸自己选择的成瘾物还足够健康,至少它不会让我成为一个潜在的对他人而言的麻烦?但我想自己一定比派瑞还要危险,因为我不仅需要它,还妄图让自己生产它。瞧瞧这个人,他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心碎生产者。但我却无法做到,那种对意象提纯的能力,令我无比艳羡,现在的我只有艳羡的份。想到这儿,我又拐回了自我贬低。说了,这东西是有着米诺陶诺斯的迷宫,但我却一点也不幸运,遇不到属于自己的阿里阿德涅,也就得不到那团让我在其中得以保持清醒的线团。
“大约是在第三十页写着:‘这些人喝酒不是为逃离,他们喝酒是为战胜一种超出他们精神控制能力的渴望。’我合上书开始哭泣。我现在只要一想到那句话就会哭。我并不孤单。有一大群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
同温层是重要的,尤其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找不到能够彼此在精神上互相支撑、互相理解的人,我想我们这类人的生活会变得更加难以忍受,精神状态也将更加糟糕。这种情况在学院可能尚且容易得到解决,但离开学院之后呢?可能有的人会说互联网和社交软件开辟了大量的空间,这是无可否认的现实。但同时,伴随这一切同时发生的并不只有乌托邦式的向好的一面,那些主动隐身的和未被算法曝光的信息流其实在展露、揭示一个潜藏的阴面。更重要的是需要意识到看似客观的那些机制本身并不客观,我想不止一个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试图寻找同好,结果却还是招来了报以其它形形色色目的的人。另一个方面,敏感群体并不一定能够或者愿意拥抱这样的社交软件,向外探寻,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对这些人而言都是要经过很慎重的考虑和下定足够的决心的。
那么似乎就只剩下唯一的途径:寻求自我脱敏?可那些无法脱敏的人呢?他们就活该忍受痛苦和这种先天性的不公吗?我们这个社会甚至不存在回答这个问题的空间和余裕,能让人想到的就只是,“是的,他们该死”,他们不仅该死,而且死后还要被戴上一切可能存在的恶名和指责。有人会说,你个傻逼你这些东西写来写去一点用都没有,我只能说我他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陷在这个怪圈里出不来,我他妈就是看不到任何与此相异的事实证据好让我能在脑子里开上一枪把这些沸腾滚烫的恶心的思绪全都毙掉。
虽然我很赞同也通过亲身实践证实了朋友能够将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将我解救,但令人悲哀的是它永远都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遇到更多其它的问题,就无计可施(让我们说得更开一些:什么也不是,就是纯粹的性,我从不愿意过分暴露自己在这方面的表现,即便是在既往的亲密关系之中,所有的一切都在提醒我他们会因为某些原因离我而去,这是我的问题,但我无法逾越这堵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高墙)。现在的我无法摆脱这种矛盾:一边说想试着建立一种超越朋友、恋人这种传统亲密关系的相处模式,另一方面却又深深觉得压根不可能。要命的是,我甚至觉得即便存在这种关系,我们也很难赋予对方所需要的那些东西。我该如何摆脱这种根深蒂固的悲哀?当我投入到实践之中,我该如何不让自己去思考“她/他们有朝一日都会离我而去”?
派瑞告诉了我他的答案:
“我深深地明白,生活是由简单的乐趣所构成的,比如来回投掷一只红球,比如观看一头驼鹿在林间空地上奔跑。我需要摆脱所有正在造成伤害的事物,比如我至今仍对父母感到愤怒,许多年前无人陪伴,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害怕承诺无法兑现而不敢承诺。
我需要记住的是,爸爸当年离开是因为他害怕,妈妈自己还是个孩子,但也尽了最大努力。她不得不花费如此之多的时间来为混蛋的加拿大总理工作,但那不是她的错——那从来都不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哪怕家里有小孩也无济于事。当时的我不明白,但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需要向前走,向上走,意识到外面有一整个巨大的世界,但它不是来抓我的。事实上,它对我没有意见。它只不过就像是动物和冷冽的空气;宇宙是中立的、美丽的,有我没我都没有区别。
事实上,我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虽然它是中立的,但我依然设法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有意义的空间。我需要明白,等我死后,我希望《老友记》在我成就清单的最后面。我需要提醒自己,善待他人——将与他人的邂逅当作一种快乐的体验,而不是一定要让自己充满恐惧,仿佛恐惧才是重要的事。我需要保持善良,好好去爱,更好地倾听,无条件地付出。是时候停止做一个充满恐惧的混蛋了,要相信,当情况发生时,我有能力解决。因为我很强大。”
我知道,我努力了,我试着让自己在他人面前表现得足够亲和友善,足够乐观开朗(如果可以我想把这两个词完全消除,就像它们从来不曾存在),试着理解他/她们如此抉择背后的那些情绪和感觉(我总觉得自己理解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却从没能被理解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足够理解)。但是我就是无法把这些该死的念头赶出我的脑子里,关于否定的、消极的、悲观的那些东西永远都要比这些该死的心理暗示来得更加根深蒂固。况且我并不相信我所身处的世界是一个所谓的“中立”的世界,去他妈的中立,该死的中立,该死。他们为什么要在我年轻的时候将什么理想、独立思考、要有承担和责任感、做一个高道德感的人这些观念灌到我脑子里,我无力改变自己的坚执,但这份坚执只会让我死的更惨(我他妈甚至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说一句“没用”都不能)。我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世界,一个你越相信越坚持那些对的、好的东西就越是难以活下去的世界?
“你在纽约,虽然有不止一个而是两个戒瘾陪护,但你还是给酒店的客房服务部打了电话,你的声音因为脱瘾治疗而颤抖,你说:‘请在我房间的浴缸里放一瓶伏特加。是的,放在浴缸里。藏在里面。’然后,一天结束,你回到那个该死的酒店房间,喝掉那瓶伏特加,终于感觉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这样的状态或许能维持三小时,然后到了第二天,一切从头再来一遍。你在发抖,每次和别人说话,你都要假装你的麻烦并不大。你用同样颤抖的声音给酒店打电话,让他们再在浴缸里藏一瓶伏特加。”
差不多得了,让我们把成瘾症这三个字换一种写法,抑郁、焦虑、强迫、双相,随便什么都好,或许得到的结果完全是一样的。我实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陷入这样一种状态,那种空虚的感受无时无刻不在追赶着我,我试图赋予自己活下去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以某种借口继续苟延残喘,因为我确实畏惧死亡,尤其畏惧一事无成的死亡,但我却没办法让自己摆脱这种几近求死的状态。每当我的生活看起来稍有起色我就还是会陷进更无望的泥沼之中,如果我能说服自己真的有病而不是其它所有让我这么想的人才是真的有病那该多好。
“像我这样的酗酒者和成瘾者,喝酒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要感觉好受些。好吧,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想要的,从来就只是能感觉好受些。我感觉不好——喝两杯酒后,感觉会好一些。但随着疾病的发展,我需要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东西才能感觉好受起来。如果刺破了清醒的薄膜,酒瘾就会发作,说:‘嘿,记得我吗?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好了,给我和上次一样多的酒,否则我就杀了你,或者让你发疯。’接着我心中的执念开始起作用,我控制不住地想要感觉好受些,一股说不清的冲动涌上来,而最后留下的是一道伤,只会朝一个方向发展,永远不可能好转。一个酗酒的人不可能轻松戒酒,然后正正常常地喝酒社交。这种病只会越来越重。”
我实在说不清相比酗酒、嗑药,自己这种空虚到随便捡垃圾去爱的人到底谁更可悲一些?之间到底又有什么真的区别?试图将自己全都掏给一个完全错误的对方,尽管感受不到一点回应也还是在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突破自己的底线,让自己没有了自己,让自己陷入在这种消融的处境之中,自我感动。这种事情也是会上瘾的,似乎只有不断进入到这样一种畸形的心理处境之中才能苟延残喘下来。为什么一定要试着让对自己完全无爱的人爱上自己,为什么愿意听从这些人的话语也不愿意听那些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的声音?为什么,在后者面前反倒只能躲闪回避?我为什么被制作成这个样子?
“阻力最小的道路是无聊的,伤疤是有趣的——它们讲述着诚实的故事,它们是战斗的证明,对我来说,它们来之不易。”
没有人有资格否定我为此做出的努力,没有人。可笑的是我所追逐的那些人,我所追逐的来自那些人的认可却从来都不存在,反倒是他们一次又一次践踏、曲解、无视着我努力的求生,一次又一次给我贴上那些我最讨厌的标签。我被损毁了,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巨大的空洞无法填补,求生的意志、意义和理想只会招来哂笑。在这些关系中,我试图反抗,但每一拳都像是打在棉花上。我该如何不让自己陷入绝望?
金钱?
我怀疑自己的能力是否真的能够赚到足够的让自己能有一个基础安稳生活的金钱。我真的能够为自己建立起一个所谓的良好的生活吗?
够了,又该被说道不够努力,自己没把握好机会。
我已经厌倦了,太厌倦了。
“活着得麻木一点。”
是不是再多做几个月鸡汤文案,我就能被“治愈”了?
我必须要去改那个傻逼的不能再傻逼的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