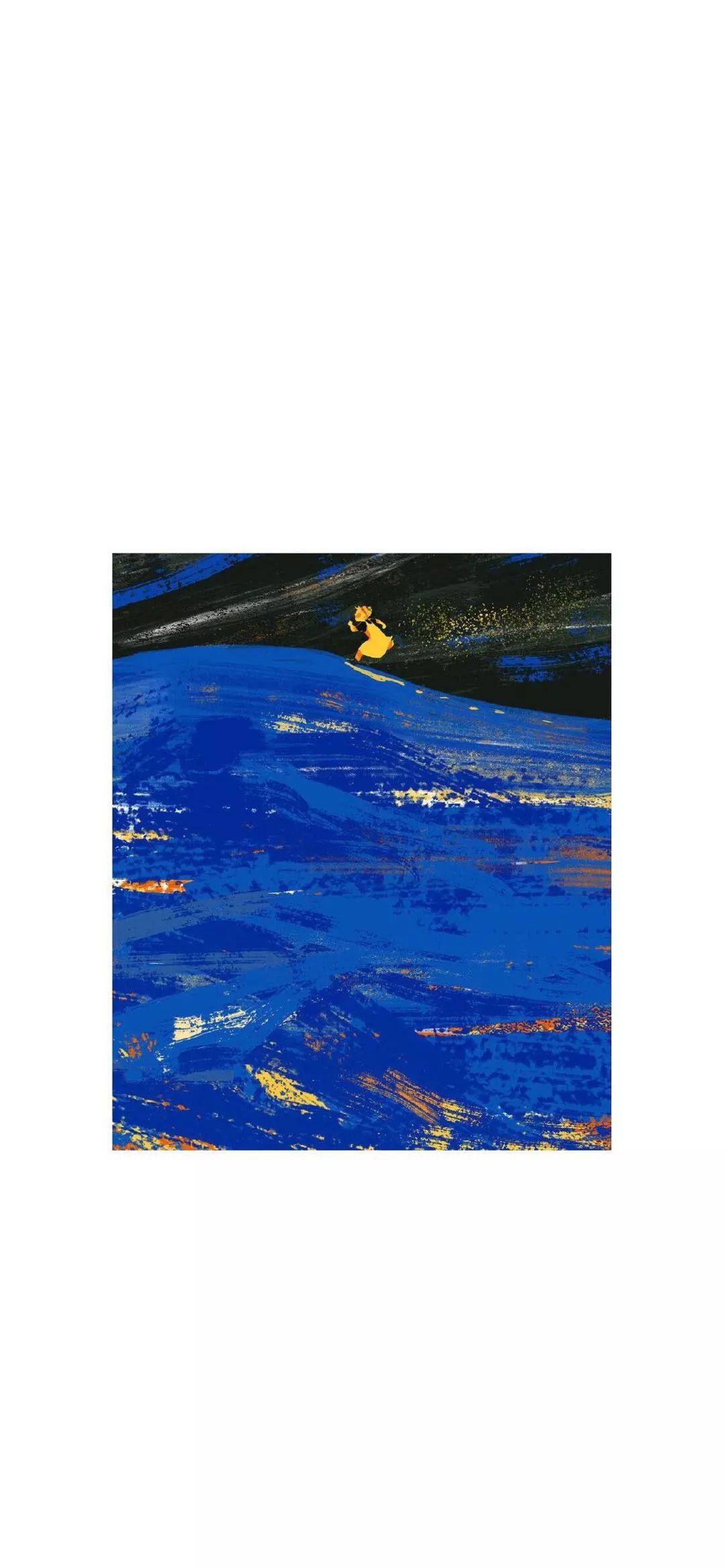A LETTER FROM PAST
Babe
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写些东西,可能这件事说起来会多少显得有些可笑,或许难以令人信服,但事实确实如此,我的文字大多数时候是留给痛苦的,我很少会在觉得幸福、愉快的时刻进行书写,是的,这很俗套,人们总是在煎熬和焦灼的时刻进行心境的宣泄。所以,请你原谅,因为这时进行书写的我,是在进行一项不那么熟悉的“工作”,请原谅我用了“工作”这个词,因为我暂时想不到更合适的词汇。是的,在书写美好的时刻,我竟然失去了对于语言的把控能力,或许是因为我根本无法平静下来,因为我知道那个我爱的人就这样贴近地坐在我的身边,我无法集中自己本就容易涣散的精神,因为我担心他,我要关注他,用更多的精力,从而在他每一次需要我的时刻,及时地出现在他的身旁。
说来有些令人沮丧,我正在逐渐失去对语言的信任感,我开始感受到当年维特根斯坦所处在的境况,也开始更加明确地理解那些令我感到无聊之极的语言学概念背后的深层哲学本质。这种不信任带来的是对安全感的侵蚀,我那本就残破不堪的安全感。我会不断地质疑自己对于文本的理解是否是正确的,我感到自己语言的失效、固化和丧失创造性,每一次书写都是一次煎熬,当然,如果在本就是情绪崩溃的时刻,书写本身便能升华为纾解痛苦的良药。在阅读的时刻,我越来越少去写些什么了,这令我感到难过,因为我去年读《在细雨中呼喊》的时候,情况还不是这样,我感到无法用合适的语词做出恰当的概括,这使我的文字一边显得不伦不类一边又令我感到尴尬不堪。或许事情并没有我诉诸笔端时描摹的那么强烈,应该说,这是我的一个缺点,通过下意识的夸张试图引起关注,孜孜以求的关注。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进行书写了。在那些未被我言说的日子里,时间就好像荡入了虚空,我再也不会想起那些时日里自己的模样,或者说,如同我经常感受到的那样,那些消逝了的回忆会在不经意的时刻回航,啪嗒,啪嗒,几近悄无声息地造访。在那些时刻,我总是很轻易地陷入沉沦,潜入那些宛若薄纱般流动的画面之中,漫无目的地游荡。有这样一种倾向,正如我试图不断地夸大我的感受一样,当悲伤的情绪席卷而来,通常我会放任自流,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但我就是不愿意逃离出来,当我被推入那个被黑暗包裹的洞穴,我总是会闭上双眼然后想着能够更快地坠落,在这种时刻我会打开令我感到无比痛苦的音乐,让它裹挟着我,用更快的速度和更沉重的力量碎裂在底部,是的,我在期待着碎裂,期待着那样一个瞬间,因为唯有在那个时刻,我才能摒除一切、忘记所有的目光,撕扯自己,聆听那些不断震荡在体内的回声,这样我才会解脱。一直以来,我都这样暗示自己。
经过这些日子,我开始逐渐撕下自己的伪装,一层一层,每一个侧面,它们是冷静把控全局的问题解决能力、是故作潇洒的毫不在乎、是总说没事的假装坚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选择在这样一个接近尾声的时刻,将赤裸的自己暴露在强光照射之下。是的,他们会发现我的脆弱是全方位的,我的不负责任是全方位的,我的愚蠢、嫉妒和丑陋面目也是全方位的,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自我呢?我不知道。我只是感到一点点痛快,这是一种做好舍弃一切之后才能感受到的痛快,破罐破摔的痛快。是啊,痛快。潜意识是个好东西,它会让你忘记那些痛,而更多地保留快感,就像这个虚假的能指一样,如果不思考一下,我们会把它视为一种令人艳羡的褒义词,这很可笑,将之认定为好的词汇的我们也一样很可笑。
我总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很多精力,逐渐开始用一种仰视的目光去看待“少年”这个词语,记忆实在是太过易于修饰了,无论多么痛苦,当你回望它的时候却总会感受到某种怀念。在我最富有理想主义的岁月里,我并不能理解它所具有的所指,而当我逐渐被磨蚀之时,我才懂得了它。朱文在《弟弟的演奏》里写过“你知道,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闪耀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性啊。”在那样一本由毫不正经的文字组构而成的文本中,他将自己最正经的渴望埋葬,这是一代人的呼声,但也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呼声。
宝贝。你说你厌恶你所身处的国度、文化和那腐败的制度,我虽然无法完全理解你的感受,但我感觉一切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可能,在阅读、经历过更多之后,你的观点会发生一些改变,抑或许你将更加坚定地走下去,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我会为你感到高兴。虽然我这么说多少会显得有些老气横秋,可这只是一次善意的提醒,如同下棋时的落子无悔一样,被诉诸笔端的文字,总是要比我们说出口的音节显得正式、令人印象深刻一些,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及的那样,“我唯一知悉的是我自己的无知”,轻易做出论断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认为这样的我会令自己感到失望,可我并不会对你感到失望,因为我相信,你做任何一件事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和理由,所以我只是提醒,而非要你认可或加以改正,毕竟,有的时候,能够选择去固执己见,也是一件令人感到羡慕的事情。
我想我已经逐渐开始进入交流的状态了。是的,我总是很难进入一个主题,很容易岔开去说些随时随地想到的事情,这是我对自己写作的一份放纵,我深知它并不会为我带来什么提高,但我不愿将这样唯一一种能够与自己交流的方式不经舍取地放弃。既然刚刚说了舍取这个词,我们就接着谈一谈你的迷茫。我很讨厌畅销书作家,尽管少不经事时的我曾无比狂热地崇拜过他们,但我还是得说,刘同那本滥俗的书的名字多少有些道理,是啊,“谁的青春不迷茫”?我见过很多迷茫的人,身边的同学、曾经喜欢过的男孩、家里的表弟甚至是我的母亲。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典型的INFJ,自己是否做到了倾听者应尽的职责,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否有资格为别人做出些解答来,但相比诉说,我似乎更愿意去倾听。我曾跟我的闺蜜说过,我很少感受到“被需要”,是的,少有人愿意和我分享他们的事情,即便是我的闺蜜也是如此,她的分手、恋爱、烦恼,都很少会直接跟我分享,只有在我一次次邀请她相见的时刻她才会轻描淡写地跟我提及,后来我学会了释然,你不能指望或说要求另一个人对一段关系投入你所投入的那么多的情感,“对等”往往只是一种奢望,但确实,我们都会忍不住去想这个问题,或许只有时间才能让它被慢慢地遗忘。我很开心,因为宝贝,你让我感觉到自己被你需要,这是一种独特的需要,因为独特,开心也变成了双份的开心。
其实,我是很羡慕你能有这样多的选择的,而且你在所有的方面多少都能有所选择,是的,选择多了也就会迷茫。这些年来,我开始认为人是自私的动物,爱的目的不是为了对方,而是为了自己被爱。正是基于这种本质性的自私,人才会变得贪婪,这也是一种人类所必须直面的本质。正像我为了专一的名头和奖金而感到闷闷不乐一样,你也会为自己无法保上很好的学校而愤懑,即便你本身更愿意出国留学。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可能你还是需要进行一个明确的衡量,即到底是要出国还是留在国内,当你决定下来之后就不要在关注另一个方面了,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切除一切与之有关的信息源,专心你所做出的选择。对我而言,这种迷茫和犹豫出现在大一下学期,我在考虑要不要继续留任学生会,考虑要不要继续留任班长,但我知道,相比所谓的锻炼机会,我更想拿到保研的资格,更想多学一些东西,因为从根本上讲,我为自己规划的道路就是一直读下去然后到大学去任教,所以最终我放弃了留任,我也曾经去面试过某杂志,但很可惜我没有被选上,那时我也很失落,但生活就是这样,岔路会不断地出现在你的面前,不应该的是持续不断地回头,然后痴想“如果当初”。是的,或许选择之后,斩钉截铁地消解多余的念想会是一个可供你参考的建议。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笨的人,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和我自己都在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只有努力这一道路可走。小学的时候,我阴差阳错地被外国语中学录取(每个小学只能有一个人被推荐过去),进入初中,我才感受到自己的鄙陋,不断的考试和不断的排名一次次让我认识到自己距离学校、老师和家长们所强调的“优秀”有着太大的距离,但好在我坚持了下来,尽管并没能拿到过很好的名次,直到最后一次模拟考试还在三十多名徘徊,中考却又一次阴差阳错地让我被高中部录取,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一直在说,这是一种幸运,是的,一种改变我人生的幸运。但似乎我没能抓住这个幸运,它悄悄地溜走了。所以,在我成绩已经有明显地起色的高二,我又一次跌落了下来。那是一次无可救药的爱恋,也是一次自缢。无时无刻的沉沦令我失去了方向,每日每夜都在幻想和痛苦中度过,最终导致了我整个高中生活的溃烂,高三再也没了起色,我开始放逐自己,每日声色犬马于游戏和刷题之中,按说,高考完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自己走向了末路。在某种意义上,来到这所学校本身也是一种报应,接下来便是长达三年的水逆,遇人不淑、缺乏经验,疲倦、焦虑、痛苦,别人学习的开心在我这里只是无穷无尽的压抑。其实我很难跟上进度,我感觉那些纷至沓来的作品令我目不暇接;我厌恶阅读文学史课本,每一次阅读都会让我感受到无穷无尽的压力,每一个书名号和每一个人名都在向我做着鬼脸;我没有读过它们,我没有读过它们,我只能感到无力感。所以我很少看课本,很少看理论类书籍,只是寄希望于多看些文献然后开始写那些没什么意义的学术垃圾,沉醉在尚且可看的分数之中,日复一日地腐烂。
这些年里,我不仅一次回想过初三和高一的自己,似乎,我所有的汗水和正经的努力都已经在那两年里透支了,所以,幸运之神降临似乎是一种怜悯,对勤勉的怜悯。
我知道她不会再回来了。
2019年,我开始不断地寻觅,我接触过许许多多的人,用尽全力去爱过,第一次当面和别人表白过,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接吻、第一次在快乐中丧失自己,结果是一次次被拒绝,一次次被践踏,被他人的自私,那些令我感到恶心的自私。参加活动的时候本来是一场美丽的邂逅,我喜欢上了一个学弟,那是我第一次,燃起想要照顾他人的想法,我们每天见面,一起训练,度过每日漫长而又短暂的7个小时,我们在凌晨的大巴车上肩靠肩入睡,在不断变换的排练地点仰望深夜里满天的繁星,我们打闹、一起玩游戏,一起吃饭,一起自习,只到这场旅途将要结束的时候,我选择将自己的喜欢告诉给他,但结果并不怎么美好,甚至显得狗尾续貂,令人感到可笑(我那时的爱显得无比可笑)。
后来,十一月的时候我和一位短暂来京出差的男人做爱,在阴差阳错的情况下将自己珍视很久的第一次交给了一个陌生人。再之后,我遇见了前任,我们的恋爱从做爱开始,到最后我也没有听过这个比我大了十岁的男人说上一句真诚且严肃的“我爱你”,可能是因为北京太冷的冬天和心已经太过乏累的我自己的原因吧。我知道那是没有结果的一次恋爱,一次从开始便注定会走向失败的初恋,一次不负责任的自渎,但我没有拯救自己的能力,我也不愿意拉着他下水,所以最后,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分手。然后就是一个漫长的自我和解的过程,我重新审视自己对于情感、亲密关系的看法,一边上课、一边阅读令人无语的沈从文、一边阅读奇奇怪怪的作品,我失去了书写自我的能力,每一次打开空白的档案,我都只能望着不断闪烁的键入符发呆,或者是在不知道如何敲击完一大段话之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我知道自己已经不愿意再写了。
但你逃不过去的,是的,逃不过去的,自我认知的爆发和书写欲望就随着春意一点点滋长,随着抽芽的时节到来慢慢地绽放。
我得绕回来了,我已经走得太远,再不回来的话,你会感到着急的。
是的,我是一个很笨的人,或许,也是一个被幸运之神暂且抛弃了的人。于感情,我木讷、稚嫩、呆笨、口不择言,很可能,我无法写出堪比洛尔迦、安德拉德那样美妙的诗篇,写不出佩索阿和卡夫卡那样热烈的告白信件,甚至连表达爱意也只会用“我爱你”,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宝贝,我是一个很笨的人,笨到我只会鲁莽无比地用尽全力去爱你。
宝贝,对不起,我只能这样,爱你。
C
202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