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读书笔记
当称赞某件事物具有开创意义时我们会运用怎样的词汇去描述它?或许我们会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来形容,抑或许我们会感觉到语言的苍白无力,绞尽脑汁也只能说出“很有价值”。不得不说,在我开始读这本赫赫有名的著作之时,这样一个问题就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诚然,它确有不足之处,但是抛却对于这些不足的评判,它依旧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正如阿尔·戈尔所言:“《寂静的春天》犹如一道闪电,第一次向人们显示出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1]引言05“(它)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以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1]引言16正是由于卡森以一种义无反顾的义士精神在那样一个世人对生态环保完全处于蒙昧状态的时代为人们未曾察觉却已然发生的危险发出迫切的警告并“试图把此问题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问题提供证据”,有关于它的一切才显得那样难能可贵。
在整本书的开篇,卡森首先引用了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的话:“我对人类感到悲观,因为它对于自己的利益太过精明。我们对待自然的办法是打击并使之屈服。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多疑和专横,如果我们能调整好与这颗行星的关系,并深怀感激之心对待它,我们本可有更好的存活机会。”[1]引言22可以说,这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正是作者观点的一个高度的概括,不可否认这一表述确实表露出某些消极色彩,但是这一总括全书的论断背后所显现出的对于旧有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与深刻反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大量现实现象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文本中主要体现为化学制剂的大量使用),卡森为我们铺展开一幅又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例如她在第一章“明天的寓言”中所抛给我们的那个令人惊愕却又无可辩驳的现实:“一个狰狞的幽灵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向我们袭来,这个想象中的悲剧很可能会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我们大家都将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1]3——这所谓“狰狞的幽灵”在文本中即是过度使用化学制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现在我们也称之为“生态危机”。
接着,通过“死神的特效药”一章,卡森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主要的、用于生产生活的化学制剂,她不无嘲讽地说道:“如果我们要和这些药物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吃的、喝的都有它们,连我们的骨髓里也吸收进了此类药物——那我们最好了解一下它们的性质和药力吧。”[1]17之所以这样讲,正是因为当时不仅仅是广大的民众,甚至于制定药物政策的管理者以及使用药物的人都对这些看似光鲜亮丽极具效力的化学制剂毫无认识,这也映证了阿尔伯特·史怀哲的名言:“人们恰恰很难辨认自己创造出来的魔鬼。”而就是在这样无知的情况下,大量的化学制剂却被投入到江河湖海与山林草原之中。
从动机来看,之所以要使用这种化学制剂,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被人类认为是诸如“害虫、无用的植物”之类的生物,但是正如她在第六章“地球的绿色斗篷”中所说的:这些所谓的“无用的生物”“之所以注定要毁灭仅仅是由于我们狭隘地认为这些植物不过是偶然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长在一个错误的地方而已。”[1]63并且“还有许多植物正好与一些要除掉的植物生长在一起,因此也就随之而被毁掉了。”[1]64在这里,卡森所批判的实际上是西方传统中“人高于自然”这一观念,当涉及的对象扩展至世间万物,那么被尊为不可轻犯的平等原则似乎在此处失去了它本应具有的权威效益,从这一层面看,我们振臂高挥的平等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不平等的观念之中,这无疑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莫大的讽刺。
笔者认为,文中的除杀工作之所以不应当被实施,是因为它已经被证实是劳民伤财、毫无益处的,更有甚者,当更为有效的环保的方式已经出现,人们仍继续采用这种无效的喷洒化学用品的方式去灭杀这些所谓的害虫和无用的植物,这时一切行为的性质就变了,这已经不再是为了“利己”而仅仅是某种意义上的享受“虐杀”。与此同时,“使用药品的整个过程看来好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螺旋形的上升运动……因为按照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这一伟大发现,昆虫可以向高级进化,并获对对某种杀虫剂的抗药性。之后,人们不得不再发明一种致死的药物,昆虫再适应,于是再发明一种新的更毒的药。”[1]8在这样不断地循环往复中,“虫药之战”永远也不会有一方取胜,而所有的生命却都在这场强大的交火中受到了无法挽回的伤害,这些化学制剂也不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恶果就在这样时候悄然播下了它的种子。
卡森通过这些现实在向世人展现人类自认为是自然的主宰时的所作所为及其带来的种种恶果的同时,又提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样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她指明人类自以为是地控制自然的做法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虽然一时的蝇头微利可以得到满足,但接踵而至的却是历时长久的危害与灾变,倘若想要从根本上去改变这种境况,就需要深入到意识层面,用一种“谦卑意识”和一种强调“与其它生物和谐共存”的新的伦理观念来接替此前人类面对自然时那种妄自尊大的态度。[4]98在这一观念下,卡森从技术层面提出使用生物防治措施代替传统的化学制剂,而这使得当时相关公司及政府机构的利益受损从而引起了它们对这位已经罹患重病的女性的强烈诋辱,在这个意义上,卡森也正如美国生态伦理史学家纳什所言,“是一个英勇无畏的女英雄,一个愿意把她生命的最后能量用于促进人与环境间建立新道德关系的伦理先锋。”[4]100
总的来说,卡森所带来的这场生态观念的革新不仅仅是对滥用杀虫剂等化学药品的一种征讨,更多的是上升至哲学伦理高度的对人类环境知识短缺与自然功利傲慢态度的一种深刻揭示与反拨[2]90,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卡森的这种观点背后所显露出的她从史怀哲那里接受的整体主义生态观。
众所周知,自然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在地球的外部圈层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即由水圈、土壤圈以及生物圈构成的循环),而“杀虫剂”和“除草剂”所带来的恶果也充斥于这三个与人类生存极为密切的圈层之中。当我们构想这样的一个循环的时候,一切都极为清晰地显现出来:首先,农人向地面喷洒含有一定毒素的化学制剂,这些昆虫、杂草在吸收这些制剂中的成分之后相继死亡,继而沉淀在这些尸体中的化学成分或是通过土壤的降解作用渗入其中,或是在喷洒时直接进入土壤;紧接着,或是与此同时,化学成分通过植被的根系以及同地下水相接触的土壤进入地下水之中(或者在喷洒的过程中就已经直接进入了河湖)。当水中的化学物质含量超过一定的限度,污染就会通过水圈循环逐渐蔓延至整个生物圈:河湖中的生物迎来死亡,以鱼类为食的更高层级生物,诸如鸟类也会因为在食用受污染的鱼类之后使毒素在体内积聚从而致死(人类也同理)。
除此之外,当人类在已经被污染的土地中再次种植农作物时,土壤中所存留的毒素也会直接渗入作物之中,而这些食物最终将会流入人体。同食用鱼类一样,曾经极为微量的化学成分在食物链的浓缩与层层积聚之后所形成的数量是难以预估的,倘若这些含有毒素的生物最终进入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的体内,那么其危害就不言而喻了,而且正如我们所知,这些积聚和浓缩的过程是悄无声息的,只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而那时已经为时已晚。
卡森在书中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惊人的案例和数据来揭示这些在表面上看似并无大碍的假象,然而即便如此,这还不是最为可怕的情况,最令人担忧的事情是:当全世界的化学家们兢兢业业地进行着实验研究以推动化学工业的发展时,我们却难以测定经由大自然这一天然的“新药物的化学实验室”之手所产生的化学药物的成分,面对这些新物质“卫生工程师只能绝望地称这种新化合物为‘污物’。”它们还没有开始认识那是些什么东西,这些物质对人会有什么影响也无人知晓。[1]40
就是这样,在人类一次又一次运用化学制剂“征服”并试图证明自己已经“征服”自然的时候,其所显示出的结果却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卡森在阐述一个试图通过除草剂杀死“野草”的案例时评论道:“我们看来是虚弱得可悲,因为我们竟能容忍这样糟糕的景象,灭绝野草并没有使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对人类又一次这样征服了这个混乱的自然界并不觉得欢欣鼓舞。”[1]72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效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我们的灭亡,同时也愈来愈将我们拖入一个不仅仅是有关科学更是有关道义的问题中,“即是,任何文明是否能够对生物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而不毁掉自己,同时也不失却文明应有的尊严。”[1]99
显然这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每种杀虫剂之所以被使用只是基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即它是一种致死毒物。因此它就毒害了所有与之接触的生命。”[1]99当人们继续沉迷于简化大自然赋予大地景色的多样性时,人们正在不断毁坏掉的其实是自然界的平衡与格局,而正是这种平衡才造就了包含人类在内的生物物种。同样的,当我们“默认对活生生的生命采取这样使其受苦的行动,作为人类,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不曾降低了我们做人的身份呢?”[1]99在这里,卡森再一次提醒我们,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孤立存在的东西”,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整体。
那么,要如何去做呢?
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观念,观念提出是为了引导人们去实践它,正如卡森在文中所提到的,通过生物之间互相竞争的机制去抑制丛生的杂草,通过引入无害天敌的方式去治理虫害,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去盲目地寻找抑制甚至灭绝这种植物或那种动物的技术方法,而是去了解关于动物繁殖和它们与周边环境的关系的基本知识,并且在此基础上去建立区域内生态稳定的平衡,从而封锁住危害生物爆发的力量以及新的入侵,因为只有“我们关注宇宙中自然奇观和客观规律的焦点越清晰,我们破坏它们的尝试就越少。”
这也正蕴含着卡森此前所透露出的整体主义生态思维观与生态系统平衡的自然主义诉求,她意在借此告诫人类:“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应当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后归宿,成为一切行为、政策和发展模式的最终判断标准。”[3]97唯其如此,生态系统的有序完整与健康运行才有保障,人类的长久生存与持续发展才有希望。[2]92
由此看来,通过这本书卡森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从表面的悲观之中生出的对于未来的一种期望,所以她愿意事无巨细地举出各式各样的实例然后告知人们应对的方法,在这个层面上,这也可以视为是她对“人类已经失去预见和自制能力,人类自身将摧毁地球并随之灭亡”之论的反驳。
然而,我们需要质疑的是,在半个世纪之前已经得知了事实真相的人们是否做出了改变?笔者认为,在某些层面上可能确实改变了,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改变也仅仅是在极为有限的程度上进行的,这从全球环境局部好转却整体持续恶化的现实中可以得到印证。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光鲜亮丽的数字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的是环境渐趋恶化这一不争的事实,诚如梁从诫先生所言:“追求富裕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之一就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负荷的增加。”这也确实是难以避免的,但近年来有关环境污染的问题“你方唱罢我登场”就不禁使人产生疑惑:在已经有了西方前车之鉴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最后却还是同样踏上了这条“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我们又是否真的能够在不预支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的情况下迎来当代人的“美好生活”?[1]中文版序3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当我们追忆往昔岁月,伴随着那一份份深入骨髓的记忆出现的往往是现代人常常呼唤的碧海蓝天以及树树繁荫。当人们为了城市的发展能够昂首阔步地进行下去而将本已稀缺的植被连根拔起时,我想,一同被除去的可能不仅仅是一排又一排行道树,那些植被所建构的生态环境以及那些曾经生长于斯之人心中最为珍视的记忆可能也随着那一声声轰然倒塌的声响而一同消散了吧……
参考文献:
[1] [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 夏承伯,包庆德.细腻报告文学话语背后深层生态主义逻辑: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生态哲学思想解读[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第5期).
[3] 王诺.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J].国外文学,2002,(第2期).
[4] [美]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94-100.



.jpg)
.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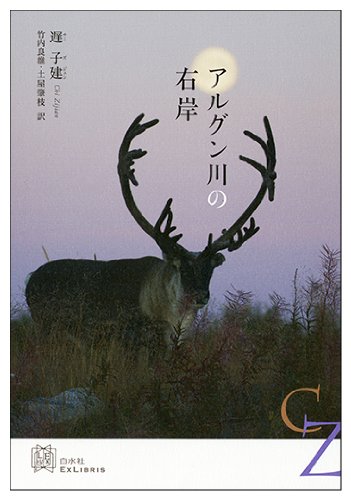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