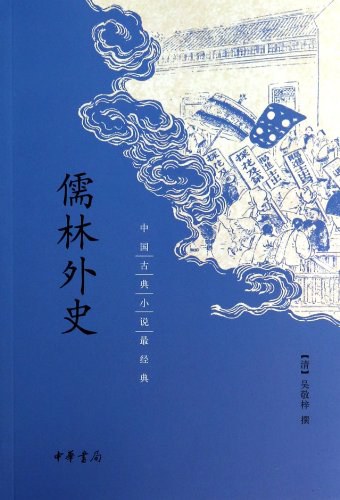谈谈魏晋风度
【摘要】汉末以来的社会动荡等原因促使魏晋文学中“雅好慷慨”风格的形成,其背后体现着时人对于如何生存于世的探讨。在政治社会上的动荡、儒家思想的影响、玄学的高扬以及东汉以来个人精神的发展多个方面的影响下,时人形成了清谈隐逸、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佯狂疏放这三种对待“生”的态度,实际上这其中蕴含着“人的精神觉醒”这一更为深刻的主题。
01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魏晋时期在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人的觉醒”这一现象,而笔者认为,魏晋士人所持的生存于乱世的三种态度即是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精神觉醒的重要表现。
[1]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7页。
02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乱世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慷慨”即是心中积郁的不平之气,换言之则是时人并存于心的人生之忧与济世之志,而“梗慨多气”则是对于这一时代文学上特点的一个高度概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特点,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军阀争权,以及严重的灾荒和瘟疫[2],而文人名士常常有颠沛流离、转徙沟壑的经历,从这种经历中产生身世无常,人生短促的亲身感触。
[2] 严重的灾荒致使许多文士迫不得已地屈尊顺从他人,诸如马融;而瘟疫更是使得“建安七子”中的陈琳、徐干和应瑒纷纷去世。
这种感触其实从《古诗十九首》已经开始出现:虽是“生年不满百”但内心却“常怀千岁忧”;因为动荡的时局和长年的战伐而常常感到“人生寄一世,奄怱若飘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而面对残酷的现实目光所及又常常是“出郭门相视,但见丘与坟”(《去者日以疏》)。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3]
[3]李泽厚:《魏晋风度》,《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以曹丕为例,他虽已极人世之尊荣,但仍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帝王将相、富贵功名终成一抔黄土,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而诗文则是这思想与精神的最佳承载者,所以他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强调著文于世以期思想的长存,而这和前述的“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悲慨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4]这种不断反复的“慷慨悲叹”实际上反映出的是时人对于“生”这一主题的深入思考,而这种个人对自己生存和发展以及生命意义的重新思考和探索正是魏晋时期个人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反映。
[4] 李泽厚:《魏晋风度·人的觉醒》,《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03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魏晋知识阶层给出了三种对待的态度:一是更多受到玄学思潮影响而形成的的清谈隐逸之风,二是为提高生命的质量而追求的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三则是追求精神自由的佯狂与疏放。而这三种态度其实是在政治社会上的动荡、儒家传统的入世思想、玄学之风以及东汉以来个人精神的发展这多个方面的影响下形成的。
首先,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一种态度是清谈隐逸之风。在笔者看来,它主要受到魏晋玄风和东汉以来知识阶层思想转变的影响。所谓清谈,这里引述鲁迅先生所言:“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起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5] 由此可知,清谈承接东汉清议而来,而这种清议则是受到东汉以来知识阶层思想转变影响的结果。
[5] 鲁迅:《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91793736/,2016年10月12日。
在东汉前期及中期,士大夫树立起了一种以理想人格与道德精神为基础的文化群体和阶层,他们把人的价值高下系于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精神上,并试图以知识阶层对文化的垄断来恢复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地位,但在政治权力的巨大威压下,这种失衡的对抗终究难以维系,最终在两次党锢之祸后走向了幻灭,此后,士人们又引出以个体生存为中心的思路,转向求取个人精神的独立与自由。沿着这条道路,曾经被奉为圭臬的儒教纲常渐渐走下神坛,而处于边缘地位的老庄思想则逐渐兴盛,从扬雄好《易》作《太玄》,王充好道家之学,晚年作养生之书,张衡作《思玄》、《归田》、《髑髅》三赋,马融好《老》、《庄》之学,一直到仲长统明显的道家知识趣味,这些种种迹象其实已经暗示了时代思想与学术兴趣的变化[6],更不用说桓帝于公元166年正式祠老子于宫中这样统治阶层层面的转化[7]。
[6] 参见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四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2-313页。
[7] 事见于《后汉书·祭祀志》,原文: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
这样的思想领域的渐变最后形成了玄学思潮的兴起,时人的关注点从品评人物转移到对“有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名理”之变和“形神”之辩等形而上问题的探讨,而玄学思想则借此更进一步地介入传统儒家思想(上述的辩论主要是通过注解经典的方法表述出来的)从而使之更加向时代思潮的外围挪移。在笔者看来,这种情况一方面因其本身已有的风气使然,另一方面这种思潮本身也助推了这一风气的发展。
对于清谈所涉及的内容,这里以“言意之辨”为例: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在“言”与“意”的辩论中逐渐形成了轻“言”而重“意”的观点,而这与追求超越境界的风气在思路上实则是一致的。在思想层面,“它引起的是精神上超越俗尘的玄远之思以及人生上的摆落形累的幽远情趣”[8],这种思想发展到生活中则产生了不少希求隐逸山林和妄图不问世事的士人 ,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与世事未能忘情。”[9]这些士人为了自身思想的独立,不愿委身于世间的准绳和黑暗的朝局,转向山林与田野,从这一层面看,确实可以说是魏晋时期个人精神觉醒的一种突出表现;
[8]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四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8、329页。
[9]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北京:同心出版社,2014年。
而这种思想延伸到文学层面则形成了时人追求创作出诸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赠秀才入军·其十四》)这种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的作品。其他清谈的内容诸如“名教”与“自然”之辩则形成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随着陶渊明对此的践行和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对于此后的整个中国文学乃至士大夫的思想精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相对于清谈隐逸,建功立业积极入世的进取态度则主要是承继了儒家的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魏晋初期,一些士人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他们再次对功名产生了欲求,加之乱世时局和内忧外患,种种复杂的情况与变革之际的思想共同构成了他们心中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望,所以我们能看到《短歌行》中“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豪迈气概,以及《白马篇》中“幽并游侠儿”“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拼死报国之志。
在以上两种态度之外,笔者认为以“竹林七贤”以及看似无念于政治而归隐的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士人们虽然在表面上沉溺于畅怀豪饮之中,“但愿长醉不愿醒”,但这种佯狂态度的背后是怀有愤世嫉俗的情感以及沉郁的入世之心的——因为时代与政治的黑暗与自己内心志向的极度背离致使他们只好以醉生梦死的态度对待险恶的世道,他们内心虽然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只能隐而不显,这里最重要的代表要数阮籍。
从其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我们大致可以读出其本人将自身人生的慨叹和哀伤同当时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迫害相连接后产生的“感伤、悲痛、恐惧、爱恋、焦急、忧虑,欲求解脱而不可能,逆来顺受又不适应”的复杂情感。虽然他想要在艰难而又布满荆棘的世路中“一飞冲青天”“抗身青云中”[9],但是现实的残酷逼得他只能低下头来,应付环境,以保全性命。所以他“一方面被迫为人写劝进笺,似颇无聊;同时又‘口不臧否人物’,极端慎重,并且大醉六十日拒不联姻……”[11]怀着巨大的矛盾与痛苦,他只能将自己放诸饮酒之间,看似逍遥,及时行乐,然而真正的内心却是呈现在“穷途之哭”中。
[10] 均出自阮籍《咏怀八十二首》。
[11] 李泽厚:《魏晋风度·人的觉醒》,《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事均见于《晋书·列传第十九》,原文: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阮籍的情况在这一时期具有典型性,从他推至这一时期的知识阶层,我们似乎就能够理解那些名士们“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的言论以及佯狂疏放的行为举止,这些实际上“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时人)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12]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及时行乐以及上述的佯狂在很大层面上是时人为了保存自身,让人格、精神以及生命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最大的舒展从而不负此生所做出的妥协。
[12] 李泽厚:《魏晋风度·人的觉醒》,《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04
纵观这三种态度,它们都在某些层面上反映着当时知识阶层对于个人精神觉醒的某种自觉追求,并且往往共存于士人心中,这种融汇造就了这一时期士人独特的复杂心态亦标志着他们走向了精神的觉醒:
清谈隐逸之中对于形上之学的关注体现了魏晋名士在走出传统儒教的束缚的同时向思想自由的境界迈出了一大步;时人的狷介孤傲、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归于山林则显示出他们内心对于当局权势的鄙弃和心灰意冷,亦展现着他们对于个人精神自由的追求;即使是希求能够杀敌报国名扬万世以逞己欲的济世之志亦不是仅仅为着儒教的教化而更多的是为了自身能够永垂青史。
无论如何,这三种态度都是魏晋时期士人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从自我出发而做出的选择,不再被武帝以后经学传统束缚下的价值观念所绑定。从怀有三种态度的不同的名贤雅士的诗文作品与行为处事的方式中我们能感受到其身上所高扬的个人精神觉醒的光辉,他们同那个时代一起,共同谱写了一曲高唱着“人的觉醒”的慷慨激昂的乐章,在之后甚至今后的岁月里它还在不断地响起,引着我们共同畅想那个饱含着“魏晋风度”的时代的风貌!
感谢阅读,
祝安
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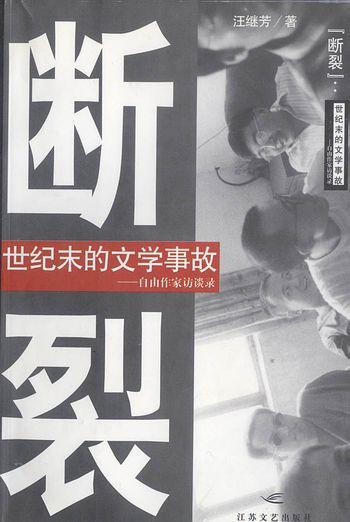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