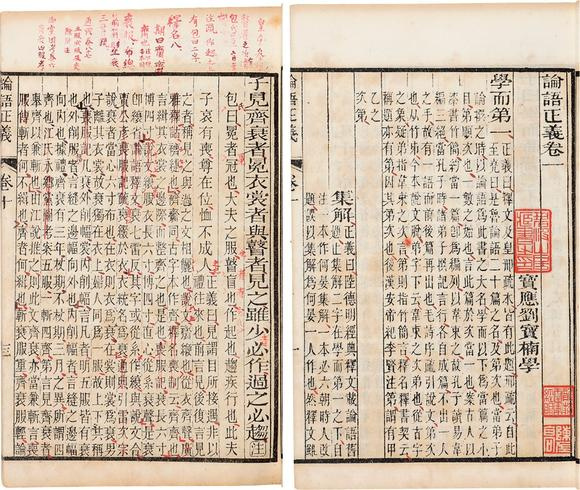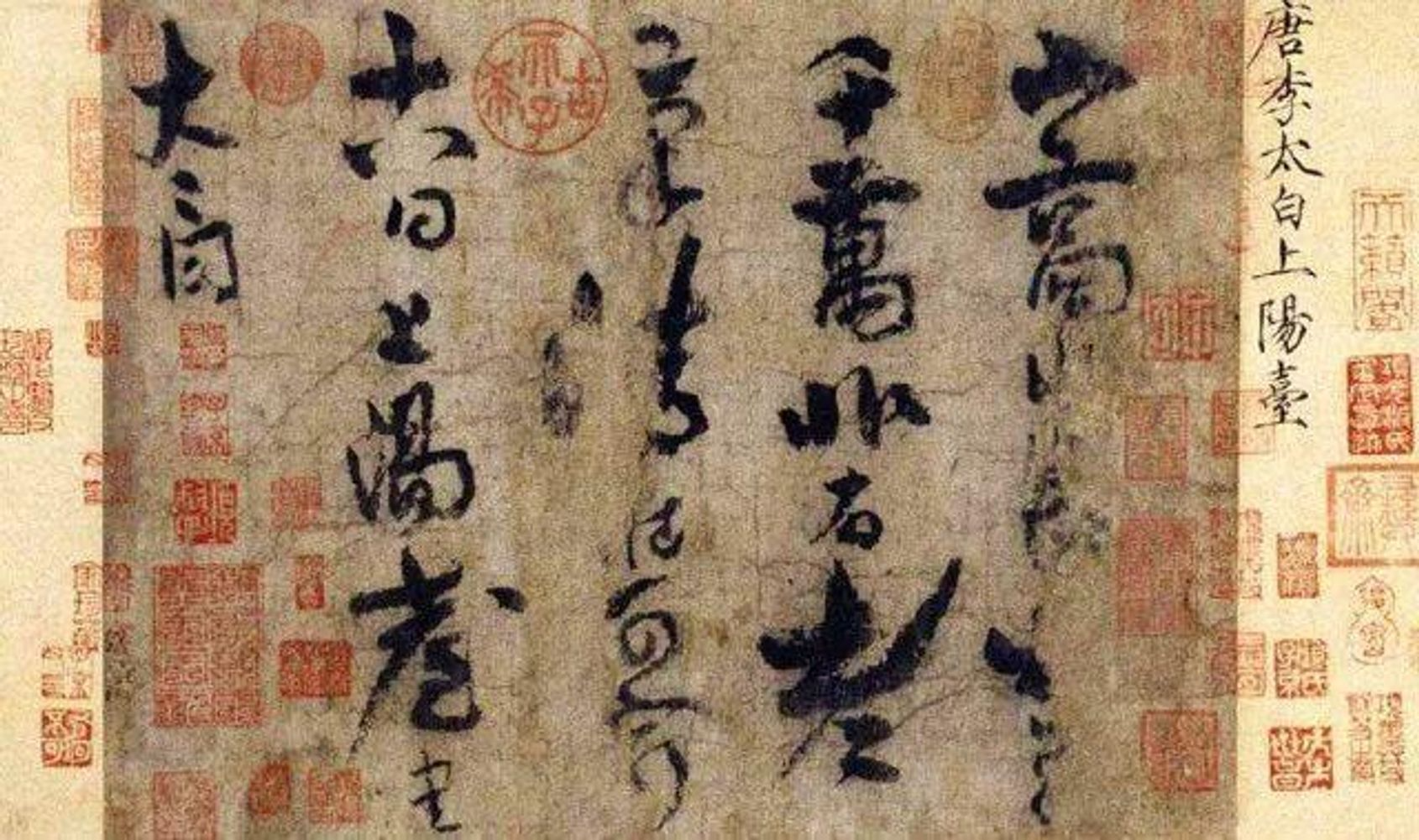“白璧染瑕” ——论余特余持兄弟形象的矛盾性
摘要:
兄弟形象众多是《儒林外史》的一大特色。出现在后半部的余特、余持兄弟被作者视为是“从古没有的”。高调肯定的背后与文本中的形象有一定的距离。五河县被塑造为恶赖之地,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情绪化色彩。空间书写含纳了各式各样三教九流的人物,建构显示出作者的刻意性。二余兄弟之间友悌重孝的特点与私和人命、抗命诡辩的行径揭示出“以伦理道德来瓦解伦理道德本身的神圣性”这样一种儒家伦理教化内在的矛盾。“贤而不贤”反映了地域空间乃至整个时代对个体的侵蚀与个体对它们的拒斥这样两种角力行为所构成的困境,书中人物以及吴敬梓本人均难以逃脱。
关键词: 传统伦理道德 五河县 余特 余持 矛盾
《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在书中塑造了大量的儒林士子形象,而其中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不少是以兄弟关系出现的,无论是早已映入人心的严监生和严贡生,还是后来接连出现的娄家二位公子,甚至在小说中最为作者重视的杜少卿也是与其族兄杜慎卿前后相继出场的。纵观全书,兄弟形象可谓是贯穿了整部作品的始末,而笔者将要在此处做出分析的余特、余持兄弟二人,无论是在出场的时机还是作者为之赋予的形象特色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尤其是作者对二人形象中矛盾性的刻意摹绘与小说后半部所着力刻画的五河县这一地域空间之间构成了复杂绵密的关系,因此,笔者在本文中通过对二余兄弟在小说中所呈现出的形象进行梳理,来试图解释二余兄弟矛盾性背后可能存在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在进入具体的文本分析前,有必要对目前学界对余特、余持形象的看法进行简要的介绍。目前的研究成果分别体现在文本研究和人物原型考证两个方面。
在文本解读方面,陈美林先生对此关注的较早,由于其观点是在贴合文本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细致入微的分析考证,并且与目前学界对吴敬梓思想观念和《儒林外史》主题的主流意见相契合,因而被后来的研究者加以采纳,成为有关这一问题的主要看法。这些论者将余特、余持视为符合吴敬梓对于兄友弟恭这一伦理道德标准的正面人物来看待,并且都指出了余家兄弟不同于小说中被作者标榜出来的其它“贤人”——二人身上体现出一种行为和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这可以被归结为古代士人所面临的“忠孝难全”的伦理道德困境。后来的研究者如陈兮和华德柱等人在陈美林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将二余兄弟归纳入吴敬梓在小说中所创作的兄弟形象这一序列之中加以考虑,试图通过这样一种相对宏观层面的归纳,来把握兄弟书写背后显示出的原作者对传统社会中的兄弟关系及伦理道德观念等问题的态度,以期揭示他书写如此多的兄弟形象的意义和目的所在。
而在原型考证方面,正如金和跋语与鲁迅先生在《清之讽刺小说》中所指出的——“《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1]二余兄弟作为小说后半部中相对重要的人物,吴敬梓在创作时也是基于一定的原型来对他们进行塑造的。由于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独特性,何泽翰先生早在上世纪就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其结果证明二人是与吴敬梓有着密切关联的金榘、金两铭兄弟,前者不仅是吴敬梓堂表兄弟而且又和他有着僚婿的戚谊。在何先生所列举出的详实的材料下,笔者认为其考证是准确的,且这样一种考证同样为我们理解这一人物形象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从而让已经脱离当时现实的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吴敬梓在创作过程中对人物与原型之间的改动与这份改动的内在意涵。
至此,经过对此前已有文献的阅读和总结,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对于余特、余持两个人物形象的研究似乎进入到了一种停滞的状态,尽管下面将要陈述的基本观点仍未能超出前辈学者所指出的范围,但笔者仍旧试图再度介入文本,从空间与个体之间关系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对余特、余持两个人物形象做出自己的判断。
二、“恶赖之地”——五河县
首先我们来看二余所在的社会空间——五河县。
余特、余持所在的余家本与小说后面出现的虞华轩所在的虞家均是五河名族,但由于近年来两家持续的科名蹭蹬而逐渐式微,后来居上的彭家和方家分别靠着自家在官、商二途的发迹迅速在当地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取代了原本余、虞二族所具有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民风的迅速转变。
在小说中,吴敬梓将五河县设定为了一个极度势利的“恶赖之地”,并赋予了身处其中的二余兄弟以“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特征,因此二余兄弟一出场,作者便指出了他们与所处的社会空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五河人的“非方不心,非彭不口”,“非方不亲,非彭不友”的“四非准则”在余特、余持那里失了灵,前者游历于四方寻求合适的人家坐馆教书或入幕,以维持家中生计,后者则留在五河,在主持家事的同时一心一意攻读备考,他们自始至终均未对新晋的望族——彭、方二家表现出任何依附倾向,甚至堪称怪异地刻意与彭方二族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另一方面,他们虽仍旧不断寻求入仕的机会,但却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将做官与发财看得极为重要。为父母办理丧葬事宜之时,他们更是趋于实际和伦理道德的考虑来决定如何处理父母的棺木葬所,这与五河县人对风水如何败坏自身财运官运的迷信行为之间也有所不同。而对此展现的最为集中的几处书写分别为余持处理余特案时发生的诸多琐碎事件、二余葬亲所引发的“风水之争”、虞华轩请余特坐馆一宴和方、余、虞三族入节孝祠一事。在这四个小的情节单元中,吴敬梓通过对唐三痰、唐二棒椎、赵麟书、余殷、余敷、姚老五、成老爹等一系列小人的丑恶嘴脸的摹绘,揭示出整个县城是如何被深深裹覆在互相勾结的官、商、绅三股势力所建立起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网络之中的。
在第一处情节中,唐三痰对余持的提议看似是为解除余家危机所提出的“良策”,但实际上一句“不然,我就同你去”径直暴露出他的所谓关心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接近彭、方二族的机会,看似乐于助人,实则仍是将己之利益放在最先位置加以考虑,“助人”不过是“助己”所顺带的。同样的,妻舅赵麟书为余持出的“解忧”法子虽是好心,但一方面暴露出“铮铮响的乡绅”是有多么令人惹不得,另一方面也揭示出“舍人为己”观念在当地人们心中的理所当然——不管这人究竟是否是手足兄弟。从一个“别人家的棺材”即可看出五河人对于伦理道德的淡漠和不屑一顾,而与之同时出现的却又是对于县内权贵的巴结和敬畏,两相对照更可知五河风俗之鄙陋可憎。
如果说第一处情节还算是带有危急的正剧气氛,那么“风水之争”则完全近乎可笑的滑稽剧了。从余殷“劈手就夺过来”的毫无礼节到他头左右乱晃“歪着嘴乱嚼”土块,从余敷上看下看到对土又嚼又嗅最后做出个看似正经的批判,两处穷形尽相的刻画已经奠定了整个情节单元的滑稽性和讽刺性,也正合卧评所言“活色生香,状形状气,如在目前也”[2]。与余特、余持的和稳持重相比,余殷、余敷一个无礼一个口若悬河,可谓在亲族兄弟面前丑态毕露,而如此装腔作势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践行一套“以葬代发”的风水观念,即“只要葬得好,就必能高中”。笔者认为在这种观念背后暗藏的实际是坐享其成的寄生虫式的生存态度,这种态度的最终指向也不出一个“利”字。
随后,经过短暂插入虞育德离开南京的“三山门贤人饯别”,吴敬梓又将笔锋转回对五河人“势利熏心”的书写上来。继唐三痰之后,其兄——“前科中的文举人”唐二棒椎也打着“恭喜开馆”的名号踱入虞华轩的家里混吃混喝,他奉上的戏码是“科名压倒一切”。如果说唐三痰仅仅给我们以势利伪善的观感,那么唐二棒椎则显然带有一种丧失伦常的特质:因为与侄子同年同门中举便要用“门年愚叔”来回对方的帖子,甚至恬不知耻地拿此来四处问询,似乎唯恐他人不知自己有个在京里生活的举人侄子。在他那里,舍侄由于“在京里”便天然带有一种优越性——仿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乎规制的,即便不合规制,由于是“在京里”,这种“不合”也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合法性。唐二棒椎身上所显示出的实际上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中央集权的制度带来的结果是越接近世俗权力中心便越具有行为话语的模范性和塑形它们的权力。在唐二棒椎这里,原本应当是为儒家经典确立的礼教政治由于无法直接为个体带来利益而失去了其本有的权威性,替换它们的则是权贵的品味和习性。对于唐二棒椎和他所戳破的姚老五以及后面出场的成老爹而言,迎合权贵的目的是为了换取自身的利益,它们或许仅仅是一顿饱餐又或许只是毫无实际价值的吹嘘资本,但就是这样一种可能存在的利益成为了他们放弃一切伦理纲常和礼义廉耻道德观念的驱动器。因此,成老爹和姚老五竭尽全力将自己的一言一行与彭、方二族挂钩,唐二棒椎不惜失去长辈的仪面也要巴结在京里的小侄子。他们在采取这样行为的过程中甚至呈现出一种乐此不疲的心态,即便有一两次“翻车”的表现也挡不住他们再度向着名门望族前赴后继地奔去的热情,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之中正如天目山樵所言“遍地如此,岂特五河”[3],可谓是贯穿全书始末。
同样的现象在五河县最具代表性的入节孝祠一事中得到了最深刻地体现。此次五河的方、虞、余三族均有逝者入祠,这本应是全族惦念注重的大事,但极具讽刺性的是,“余、虞两家的举人、进士、贡生、监生,共有六七十位”,“余、虞两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却无一例外地都在入祠前恭恭敬敬或者慌慌张张地站到方家的队伍里去了。同为望族的余、虞族人在这等道德礼教大事上却尽数心甘情愿地成了方家的帮闲,仅有“七八位走过来作一个揖”,即便如此却还是最终“簇拥着方老太太的亭子进祠去了”,世态炎凉,可见一斑,也不怪余特痛呼:“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吴敬梓塑造了一个极尽寡廉鲜耻的人间“恶赖之地”,尽管此前他也塑造了诸多恶俗士子的形象并将之和地域相勾连,但那些人物形象基本上都是空间中的独特个体,透过他们所牵扯出的次要形象也相对较少。换句话说,《儒林外史》在四十四回之前对于地域的书写从来没有像五河这个地域空间一样集中含纳了各式各样、由上层人物至下层的诸多人物,而且在书写五河县伊始,作者少见地主动跳脱出此前简淡节制的客观化文本叙事特征,对这个空间做出了整体的情感价值判断,并将相较而言富于情绪化特点的文字付诸了笔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吴敬梓通过深刻的批判讽刺手法刻画出五河县中的诸多人物形象,实际上是为了表达他对这样一种势利熏心、寡廉鲜耻的社会风气的深恶痛绝,而且第四十六回回目的直接比对,在某种意义上也揭示出泰伯祠大祭本身无法匡正日趋衰颓的世风,其结果是贤人们的四散飘零和五河县这样的势利熏心之风。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再度回看这一部分书写的核心人物——余特、余持兄弟,则能够更好地理解吴敬梓为何在此放置这样两个楷模式的人物,也能够更好地理解全书的旨要。
三、“白璧染瑕”——二余的矛盾性
余特、余持兄弟由汤镇台归乡而引出,在四十四回至四十六回前半部分位于作者书写的焦点位置,在四十六回,余特从南京回到五河引出虞华轩这个四十六、四十七回的主角后,二余兄弟便顺势退了一步,成为配角。但无论在这一系列情节中发生了何种身份位置的调度,二余兄弟无疑是以承载了作者的对照意图和他所意欲弘扬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五河“贤人”形象出现在文本之中的。
二余兄弟身上最主要的特质即是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兄弟友悌、尊亲重孝这一儒家伦理道德传统,但是二者之间仍如陈美林先生所分析的那样有着明显的差异:余大先生更多是从遵礼中表现出他的孝,而余二先生则是通过守悌来引出他的孝。[4]余特的重礼是小说所着力刻画的,文本中他的两次不满都是由门帖不合礼制而生发出的,第一次汤大公子的门帖不合礼到也无碍,毕竟对方只是来求学,因而余特虽心有不满但仍能泰然处之——回绝即可了却此事;然而当他在虞华轩置办的宴席之上听闻叔侄之间互以门年以及“愚”相称一事,心中的愤懑则爆发出来,在他看来此即荒谬乃至不可理喻之事,这一情节也隐隐与四十四回中汤镇台训斥汤六老爷时的表现相呼应。然而这等表现在五河人眼里乃是“迂性呆气”,同虞华轩的狂狷一样,被人拿做背后嘲弄他的资本。吴敬梓笔法的巧妙之处正在于通过刻画余特对礼的重视来引出余家停有尚未下葬的父母灵柩,而正是这一丧葬事宜牵连出了后面一系列的事件。
余特前往无为州打秋风一方面是为了补贴家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筹措丧葬的费用。在这一段二余兄弟之间发生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兄弟二人的差异,余持由于长期留在五河家里,形成了一种谨慎的性格,因为临近府考,担心家中无人照应,因而向兄长提意让他稍安再往;然而余特更加直率,对这种问题显然并未细究,他只想着怎么能赶紧弄来银钱以保证家庭的正常运作。同样的,经由此处亦可看出二余之间实则不分彼此,两家合为一家过。兄弟二人均是持家之人,考虑的也是家族的利益,这就为后面余持不采纳妻舅赵麟书的建议埋下了伏笔,继而经由抽丰一事牵扯出后面的判讼之事和南京城与贤人们的相会。在这里,即便是身处南京无法归乡,余特也仍旧在考虑如何安葬双亲之事,亦可显示出他对孝的重视。
总的来说,余特的主要行为和他所做事的根本目的均脱不开“尽孝”二字,而围绕着“尽孝”这个核心,也无时无刻不显示出他对于儒家传统礼制的重视。相较于余特身上这种有些近乎执拗的个性,二先生余持则更为沉着冷静也更会处理人情世故。
余持的主要事迹就是帮助兄长从风影一案中脱身而出,这就不禁让我们联想起同是为兄长摆平麻烦的严监生,前者是自觉主动将自己嵌入其中,一心一意进行帮扶,后者则是害怕牵连自己而被迫出手,摆平严贡生留下的烂摊子,两相对照不难看出吴敬梓更为赞许和欣赏的是何者。在这里,余持身上显示出守悌之谊背后实际上显示出他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恪守孝道。兄长涉险抽丰得来的银两是为了将停放在家中十几年的父母灵柩下葬,深知此事关系重大的余持知道,倘若他未能在五和摆平此番案件,其结果一方面是兄长锒铛入狱,另一方面则是葬下父母之事便要再度从长计议,因而余持守悌实际上是与“孝”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此外,正如上文提到的兄弟二人之间的对话所体现的那样,二余之间实则不分彼此,是真正意义上的兄友弟恭。除余持帮兄长摆平抽丰一案显示出二人性格和处事方式的不同外,在观念上他们倒是极为相似:节孝祠一事末尾,二余看不惯权卖婆的行为挑了祭桌回家,街上对话即体现出二人的彼此互知。更难能可贵的是,友悌关系在余家两兄弟这里不仅仅是单向的[5],在余特被选为徽州府学训导之后也是力邀余持一同相往,其原因不是为了别的,只是想着“弟兄两个多聚几时”。
仅从上面提到的这些角度来观察余特和余持,我们自然可以将他们视为吴敬梓所谓的“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贤人”,并且将他们放置在整部书中,也无疑是所有兄弟形象里最为作者所推崇和赞赏的。然而问题就由此而生,小说里,他们所作所为实际与“白璧无瑕”和“从古没有的”之称之间有着相当的距离,并且他们所沾染上的“瑕疵”在某种程度上也堪称是致命之伤。
二余兄弟形象的暧昧性均出自无为州私和人命一事。我们知道,一个社会中的法律制度所建构起的是一条生存于其中的人民公众不能越过反而必须遵守的底线,而伦理道德观念则往往是位处于这条底线之上的,由社会中的个体与个体互相建构起来的心照不宣的一种准绳。尽管吴敬梓将二余兄弟定位为“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人,但却无法掩盖他们违反法律底线和伦理道德准绳的事实。经过何泽翰先生的考证,我们得以明晰地看出余特、余持是基于金榘、金两铭兄弟创造出来的,然而考究本事则发现金氏兄弟身上似乎并无二余所作所为。因而可以说,“白璧之瑕”是“白璧”的塑造者一手制造出来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吴敬梓为余氏兄弟刻意地安排了这样一种矛盾性?解答这一问题的需要将人物形象与地域空间加以联系。
身为五河县人,余特、余持身边均是势利熏心之徒,即便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他们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余持,由于他“长期居乡,在其身边颇多吏役劣绅,因此,他虽然同样重视孝梯之道,但却洞察世情,处事练达。”[6]从他摆平风影一案中不难看出他身上谨慎处事的特点,这样一种心机和人情练达正是在与乡闾俗人长期交往中形成的,所以他才会在处理整件事情时给读者一种出有条不紊和拿捏有度的娴熟感。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特性,使二余兄弟对诸多不合礼法之事产生了一种见怪不怪的态度,而在抽丰一事上,由于动机本身在余家兄弟那里占据了伦理道德的制高点,同时为生活所迫,他们在客观上也确实急需银钱,并且加之无为州州尊的引荐和庇护,这一系列因素共同构成了余特、余持在私和人命一事与后来诡辩案情之事上的有恃无恐。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或许在看尽五河世态人情的余氏兄弟眼里,自己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值一提,由此构成的心理暗示又加剧了心安理得的成分。上述仅为笔者基于文本理解所做出的个人猜想,但可以确定的是,为白璧沾上瑕疵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被归结为是“为了践行伦理道德的要求”,而吴敬梓做出这样的安排其实是在以伦理道德来瓦解伦理道德本身的神圣性,由此就体现出了他思想观念里的一种深刻的矛盾性。早先的研究者将这种矛盾归结为“忠孝难全”的伦理困境,在笔者看来,这种归纳实际上人为地框定了二余行为所打破的道德的范围,它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背后可能存在的问题的实质。因此,笔者认为不应仅仅将抗命和违反法律视为是“不忠”的体现,它实际指向的是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一个内在性矛盾。
在笔者看来,余特、余持的“贤而不贤”反映出的是地域空间乃至整个时代对个体的侵蚀与个体对它们的拒斥这样两种行径之间的矛盾,他们实际上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尽管不满足于丑恶时代所设定下的权力制度关系,但却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打破它们,因而只能在无尽的生活中与这样一种为己所不耻的现实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倘若他们尚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保持自给自足而决然独立于浊世还好(例如庄绍光),因为这样他们精神上的纯洁性还仍旧可以高照着他们,使他们认定自己是“白璧无瑕”的。然而一旦生活失去了平衡,他们便不得不陷入自己所鄙弃的囹圄之中。这时,精神上自我认定的清白与陷入泥沼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弥合的裂隙,在这种撕裂的过程里,士人陷入了一个永无脱逃之日的“怪圈”。这样一种现象普遍地出现在整个《儒林外史》之中,除余特、余持的“白璧染瑕”之外,庄绍光出仕不利后选择隐于玄武湖,杜少卿最终因郁郁不得追随虞育德而去,虞华轩的“狂狷”都是对此的体现。
**这些士子不满于(或说不愿面对)这样一个既存的现实:自己无法在那样一个已经被科举制度和封建官本位体制所固化了的时代和社会中完成对于“功名富贵”的追求。**但对他们而言,却又同样无法摆脱这样的社会,来让儒家教化下所印刻于胸的那份人生价值得到实现。因而出现了上述的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从本质上看,这不仅是个体与时代之间的矛盾,同样是中国传统儒家理念所带给士人的理想价值观念与冷冰冰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而作为传统士人的他们却只是因为这样一种矛盾的存在而感到寂寞悲哀以及深深的痛苦激愤,他们只是也只能接受这样一种无可改变的现实。传统礼教所强调的理想化一方面使他们在这样的黑暗社会中感受到压抑和个人的苦闷,但另一方面却又成为深化压制他们发泄这种不满的伦理机器,这就构成了一个毫无出路的闭环——即他们被压抑,但同时他们却又只能选择继续被压抑下去,任何出格的事情会更进一步加剧他们身上所承受的压抑,所以他们只能够忍耐,忍耐不了而做出轻微的发泄就被世人冠以狂狷、隐逸等等名号——即便这些名号仍旧是在极度压抑自己悲凉情绪的结果。
因此,可以说吴敬梓对五河县“贤人不贤”的刻意塑造揭示出的是一种极度痛苦但却看似无解的现实[7]——在这样一种被固定死了的生活之中,传统士人“无止境地在忍受丧失信念,被废置、和流浪度日的生涯;既不断然反抗现实,也不完全弃绝现实。”[8]可以说,儒家思想发展到明清之际,一方面构建了一个礼乐教化的理想社会,另一方面却又扼杀了抵达它的可能(因为这种理想社会必须是既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咸炘所谓的“二余者,虞、庄之流而加拙”[9]方为确评。而吴敬梓的一生与他在《儒林外史》最后所做出的结论:“风流云散、贤豪才色总成空”(五十四回收场诗)、“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末回终场诗)也正是证明了,即便是对这一现实有着深切体察的他也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困境。
脚 注 :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节录)》,见于《<儒林外史>资料汇编》,朱一玄、刘毓忱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7页。
[2]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58页。
[3]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41页。
[4] 《儒林外史人物论》,陈美林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7-209页。
[5] 陈兮指出了兄弟观念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动情况:儒家贬抑虐敖,推崇友悌,因为兄友弟悌不仅能使家庭和睦、家道昌盛,而且这种友爱关系推广到社会,能形成尊长爱幼的良好风尚,成为治理国家的矩之道。但是,兄弟友悌观念后来渐渐发生改变。一奶同胞的兄弟由原本平等的双向对应关系转化为只强调弟对兄的单向关系,重点落在了“悌”上,过分宣扬弟之恭顺:“子弟尤当顺受而不当辩”,使弟与兄变成了主从关系。特别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从法律上确立了兄的特权。这样它便恶性地发展成“长兄为父”、“事兄如父”,破坏了兄弟之间的平等关系,导致了只重尊卑之分而轻兄弟之情的社会弊病。见于陈兮,《兄弟伦常视野中的<儒林外史>及其文学地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3期,第273页。
[6] 陈美林,《孝悌君子余特、余持》,见《儒林外史人物论》,陈美林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13页。
[7] 之所以用金榘作为原型,其意义也是在此。何泽翰先生指出金榘是“八股制度下被麻醉了的善良人物”。见于《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何泽翰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8] 乐蘅军,《世纪的漂泊者——论儒林外史群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10月刊。
[9] 《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何泽翰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参 考 文 献 :
【1】《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何泽翰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儒林外史研究纵览》,李汉秋著,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4】《儒林外史辞典》,陈美林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339页。
【5】《儒林外史人物论》,陈美林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6】《儒林外史资料汇编》,朱一玄、刘毓忱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李汉秋,《谈<儒林外史>里的严贡生和虞华轩》,《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8】华德柱,《论<儒林外史>中的兄弟组合》,《长沙电力学院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9】陈兮,《论<儒林外史>的兄弟群体》,《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
【10】陈兮,《兄弟伦常视野中的<儒林外史>及其文学地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3期。
【11】李健秋,《吴敬梓深层心态的真实投影——浅析<儒林外史>中虞华轩形象的内涵及其与吴敬梓的关系》,《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2】陈美林,《“兄友弟恭”的理想与“兄弟参商”的现实——<儒林外史>兄弟群像所体现的士人性格与命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3】胡建民,《吴敬梓的家庭情结——从<儒林外史>中的六对兄弟说起》,2004年第4期。
【14】王星慧,《看<儒林外史>中兄弟形象对当时社会文化衰落的讽刺》,《滁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15】乐蘅军,《世纪的漂泊者——论儒林外史群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10月刊。